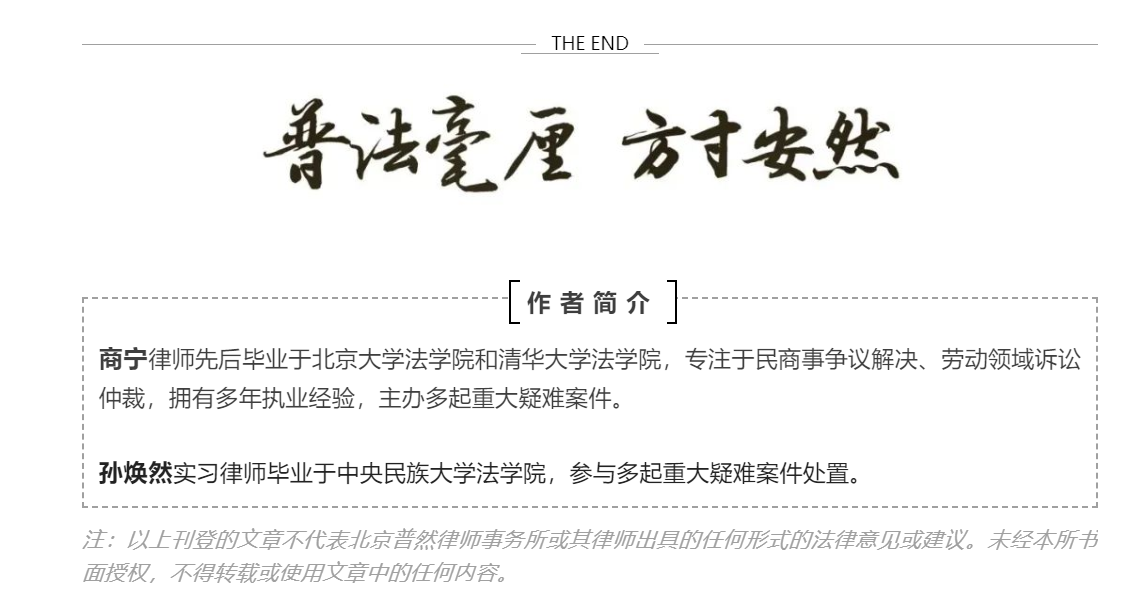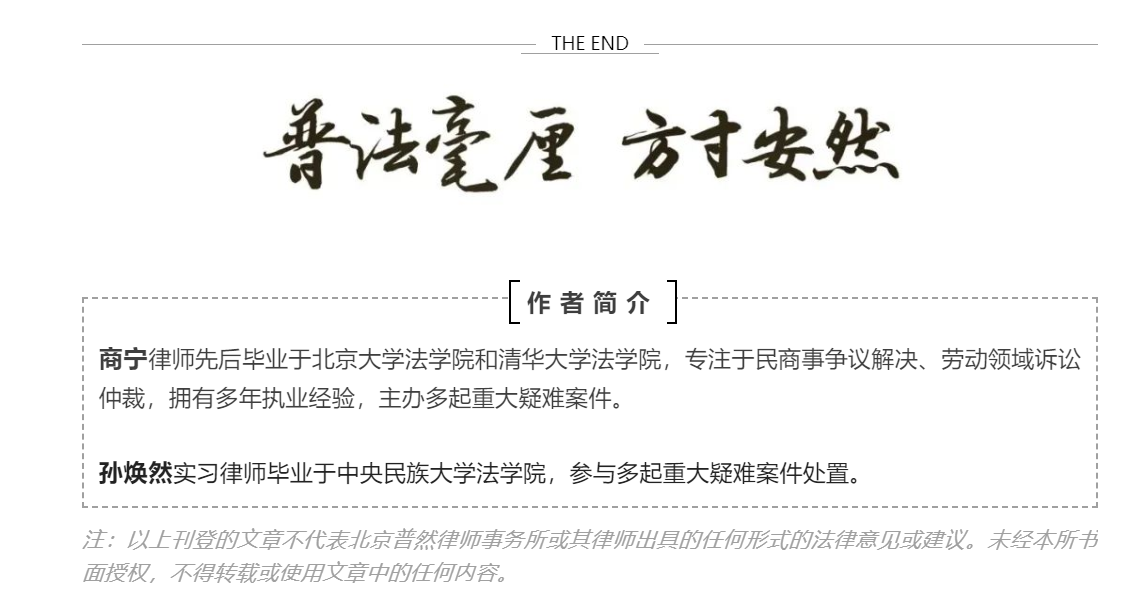司法实践中,诉请确认某法律关系存在、成立、有效,并要求相对人承担责任——即“积极确认之诉”,显然具备可诉性,根据当事人主张分配举证责任即可。但如果反其道而行,仅提出确认法律关系关系不存在的诉讼,而不做其他请求——即“消极确认之诉”,法院是否能够受理,举证责任又如何分配,却存在争议。
对此,有观点认为:“消极确认之诉”中当事人没有诉的利益,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即使受理,要求原告对于其认为根本不存在的法律关系予以举证证明,不合情理。若被告对原告此种主张进行抗辩,则势必要举证证明该法律关系存在,实际上逼迫被告提出反诉——即确认法律关系存在的“积极确认之诉”,也不合情理。若被告对原告此种主张进行否认,即主张该法律关系确实存在,则依据民事诉讼中“否认不需自证”这一基本原则,被告不需举证证明,该法律关系即告存在,更加不合情理。
对于“消极确认之诉”是否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最高院早已有定论:基于现实争议和诉的利益提起的“消极确认之诉”,符合起诉条件,法院应当受理。“消极确认之诉”的举证责任仍应按照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进行分配,即由原告对其提起的某法律关系不存在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可供参考案例
中钢集团诉信达公司沈阳办保证合同纠纷案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号】(2009)民二终字第119号、(2007)辽民三初字第103号
【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中国中钢集团公司(本文简称中钢集团)
被告/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本文简称信达公司沈阳办事处)
【基本案情】
中国银行抚顺分行与抚顺特殊钢公司签订借贷合同,其中部分债权由中国银行抚顺分行进行债转股。信达公司沈阳办从中国银行抚顺分行接收了上述借贷和担保债权,信达公司沈阳办随后刊登催收公告,向案外人抚顺特殊钢公司催收借款,债权人为中国银行抚顺分行,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即中钢集团前身)依据《不可撤销的还款担保书》对该笔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抚顺特殊钢公司拒绝清偿上述债务,信达公司沈阳办遂要求中钢集团承担担保责任,金额为1171.32万欧元。
中钢集团不认可该笔担保债务,故向辽宁高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担保关系不存在。一审辽宁高院认为,“消极确认之诉”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信达公司沈阳办先前对中钢集团的催要行为,使其在确认担保关系不存在的诉讼中,应当承担该担保关系存在的举证责任,而信达公司沈阳办未尽到举证义务,故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辽宁高院遂做出(2007)辽民三初字第10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该担保关系不存在。信达公司沈阳办对此不服,认为一审法院确认案由错误、分配举证责任错误,上诉至最高法。
【最高法观点】
(一)原被告双方关于担保责任存在与否的争议已经存在,原告具备通过诉讼尽早明确其法律地位的确认利益。原告为避免由于争议所导致的不确定性而提起“消极确认之诉”,原审法院予以受理,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二)被告未提出反诉,不应承担证明该担保关系存在的举证责任。原告未能对被告提出的足以引起法庭怀疑该担保关系存在的证据予以举证推翻,属于未达到证明标准导致事实不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普然律师案例评析】
此案是最高法审判的首例“消极不确认之诉”,不仅从司法实践的最高效力上确认了“消极不确认之诉”属于法院受案范围,更详细阐释了“消极不确认之诉”的举证责任如何进行分配。该案审判结果是,最高法二审推翻了辽宁高法一审关于该担保法律关系不存在的认定,并以提起该“消极不确认之诉”的中钢集团未尽到举证责任为由,改变了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实际上确立了“消极确认之诉”中亦应“谁主张谁举证”的裁判规则。
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的根本逻辑始终围绕“实体法律关系”,即由主张“实体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进行举证,而不考虑其并未提出反诉,而仅仅处于对“消极确认之诉”的被动应诉地位。这固然是面对“消极确认之诉”中由主张法律关系不存在的一方举证确不合理的一种解决办法,但更是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这一沉疴的体现,违背了民事诉讼的衡平原则。考虑到“消极确认之诉”具备着强迫被告进行实质反诉的机能,这种情况下被告很可能未做好诉讼准备,导致举证不能而败诉。可见,不能很好地分配举证责任,很容易使“消极确认之诉”沦为债务人逃避债务的工具,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公正价值。
最高法对于“消极确认之诉”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及其逻辑论证显然更为高明:将“消极确认之诉”的举证责任在行为意义和结果意义上加以区分。要求中钢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认为不存在的法律关系确有困难且不合理,其行为上的举证责任因无法提供证据而完成。但中钢集团仍应承担结果上的举证责任——即当事实真伪不明、无法判断时,其应当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信达公司沈阳办提供了足以令人怀疑担保关系可能存在的有关证据,虽然该证据并没有达到“高度盖然性”(被告未提出反诉,也不应如此苛责),但足以使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是为有效抗辩。中钢集团没能通过举证推翻信达公司沈阳办上述证据,自然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消极确认之诉”若被判决驳回,且对方未提出“积极确认之诉”作为反诉,则这一“消极确认之诉”的审理和裁判不妨碍对方嗣后提出“积极确认之诉”,对定分止争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一点与“积极确认之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的司法价值不同,仍会导致司法资源浪费。“消极确认之诉”纵然一经提出,法院必须受理,但当事人和律师也必须做好应对被告反诉或抗辩证据的准备,不能当然认为“消极确认之诉”就是规避法律责任的利器。这恐怕也是“消极确认之诉”的数量远低于“积极确认之诉”的原因。
(篇幅考虑,本案例严格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进行精要阐释,案例详情请见相关生效法律文书和最高法院法官著述)